2005年3月27日 台北新店
樱井:今天来到这里,主要是希望听取陈映真先生观看鄙人的剧作《台湾浮士德》后的感想,并期待陈先生就本剧与现今台湾文化状况的关联做直率批评。
陈:首先我要说的是,我对于剧场非常地陌生。原因我已经跟大造先生讲过,战后台湾的文学里面,演剧的这方面非常薄弱。这是有历史的原因。从三十年代抗日战争时期到四十年代,在戏剧的斗争方面,都是被左翼占了上风。当时出了许多左翼的剧团,左翼的剧作家,影响很大。所以,国民党对左翼的戏剧斗争非常地害怕。国民党来台湾以后,台湾没有办法自由地成立戏剧团体,不能自由地写剧本、演出。所以我的文学青年时代,差不多缺少两块。第一块就是新诗的那块。因为我开始和文坛发生关系的时候,台湾当时是Modernism(现代主义)的天下。我自己在旧书店读过一些禁书,接触了一些左翼的文学理论,所以,对Modernism(现代主义)比较排斥。其实后来渐渐明白,Modernism(现代主义)也有两种。一种是三十年代的,比较有倾向性的,是有革新性的Modernism(现代主义)。可是我们台湾的Modernism(现代主义)是很特别的,是五十年代受从美国输出的冷战文化,绘画,诗歌等等的影响。这种从美国来的Modernism(现代主义)就对于左翼的社会主义和现实主义有很明确的抵抗性。所以,我们台湾的文学,从五十年代的Red Patch以后,把三十年代进步的文学理论都统统消灭掉了。同时在血腥的Red Patch的土壤上,美国来的Modernism(现代主义)才取代三十年代的文学理论。所以,我们对Modernism(现代主义)的抵抗是从这里发展的。我也知道甚至在第三世界,也有用Modernism(现代主义)进行抵抗的,像聂鲁达。我现在比较好奇的是,我大概略知一二,不知道有没有错误。我了解到,日本的帐篷剧场是六七十年代安保斗争的产物。所以它先天地带着一种对西方、美国或者对日本追随西方体制的抵抗的色彩。这种在国民运动的抵抗之下产生的帐篷剧场,它的历史和它的性质,如果大造先生可以给我上上课,我是非常幸运的。连带着我也想知道,为什么这种大众性的抵抗,在手段上,采取非现实主义的手法。虽然,大造先生的东西,外观上看起来有Experimentalism(实验主义)的实验性,有现代主义的性格。可它绝对不是,因为它的意念性很强,Modernism(现代主义)最大的特点就是否定意念、否定主题,追求艺术的绝对的纯粹性。可是大造先生很显然有很多话要说,而且有很重要的话要说。所以大造先生的东西就不能简单地被归类到Modernism(现代主义)里来。可是它又有Modernism(现代主义)常见的那种Image。比如说,死亡的问题、尸体的问题、疯狂、腐臭的尸体的臭味、Ghost(鬼魂)、血等等。这些都是Modernism(现代主义)中非常常见的Image。可是大造先生把这些东西工具化了,不是把它当作目的。所以我觉得非常有意思。可是我的问题是,当我们的目的是要启蒙,对大众,比如说领日工资的劳动者,要对他们做启蒙和教育的时候,这么重要的意念,要用什么样的方法来表达。为什么帐篷剧场一开始就采用这样的方式。
刚才说的迷失掉的第二块就是演剧。因为我们没有剧团,学校没有剧团。没有那种小剧团,扛着布景,演练。所以,我对于戏剧是非常外行的。今天来到这里,是想通过大造先生的作品进行学习。
樱井:兴起于60年代后期的日本的帐篷戏剧,并不具有被历史化的激烈的契机,与其说它的历史,不如说在此只是介绍它简单的演变过程。并且完全是我的一己之见。从1973年到现在,我已经作了三十多年的帐篷。但这并不是说,作为一种演剧表现而使用帐篷,特别是在最开始,我们其实是因为要在日本全国巡回而依赖于帐篷。所以可以说,我们是为了从“演剧表现”逃到“流浪者戏剧”而选择了帐篷。我们一直用“帐篷戏”,而不是“演剧表现”来形容我们的行动。
在我之前,六十年代到七十年代,日本就有许多因厌倦了剧场,而搭起帐篷进行斗争的先辈。现代主义在这一时期开始渗透到大众,特别以东京奥运会为契机,一夜之间被贱价抛出的“世界”一下子在日本的面前展开。本来还稍显穷酸的老百姓突然升格为市民,并且,在超级市场里,把“世界”掂量在手中买下来的幻想开始流行。
这种情况立即反映在剧场空间中。开始有文化资本加入进来。但是,这与旧有的商业演剧不同。不是把演剧商品化,而是把演剧印象化,并使之融进消费社会的战略。另外,战后一直持续的民众剧场的手法越来越不能通用。特别是新剧现实主义的手法在消费都市剧场中无法施展。在这种情况下,地下剧场就应运而生。帐篷剧是其中的一支。所以当初的帐篷戏剧是那样的消费社会的产物。当然,也有对当时在越南战争中,对美国紧追不舍的日本政府的抵抗的背景因素。当时,确实涌现了许多追溯到前近代的表现,其中就有明确打出文化运动宣言的名为黑帐篷的集团。
起步较晚的我们,正是在对先辈们的批判上出发的。其中一个问题就是对“表现”的理解。对先辈们来说,无论如何“表现”都是重要的。相对于此,名为“表现”的其实是幻想,则是当时年轻的我们的想法。想表现些什么,想做些什么给人看,让人觉得是很资产阶级的思维方式。另外,也有对貌似抵抗市民社会而实际上很顺从的地下剧场表现者的反抗。他们也不过是翻一个个的精英而已,当时产生过这样的疑问。70年代以后,学生运动产生衰退,但也没有复归社会的心情,需要有一个逃避的场所。我们就选择了“巡回之旅”的方式。帐篷就是实施它的场。也就是一种避难所吧。当初,我们就是一台卡车上装上帐篷和人,也不定公演地就出发。到乡村中去,找到空地就搭起帐篷。然后向当地的老百姓发放宣传单,进行公演。就是模仿以前的流浪艺人吧。那正是我们帐篷戏的出发点。大概是73年到74年。
日本战后的新剧运动是经“卡车剧场”、“闹钟剧场”等开辟出来的。我们的东西可能和他们比较接近。但是我们没有中心队伍,也并不是要启蒙什么。因为是要破坏剧场性的剧场,所以,当时对观众来说是很大的麻烦。
陈:布莱希特也曾提倡要破坏剧场。
樱井:接着刚才新剧的话题,当时是有布莱希特和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路线。当时日本的新剧运动被制度化了。也就是通过“劳演”(劳动者演剧协会)理顺关系,是一种职业性的演剧。这样一来,在职业化的笼罩下,实际上有共产党和社会党的方针若隐若现。六十年代的安保以后,与新左翼登场同时,开始出现批判者中构造的戏剧人。
陈:中国的演剧运动也是党领导嘛,地下党的领导。在中国就没有产生这种内部的自省。这大概是因为日本的党没有像中国的党那样节节胜利,得到人民的支持,而是有停滞期。
樱井:在六十年代,包括中国的文化大革命,世界范围内对旧有的制度和文化的质疑一下子喷发出来。可是,据与我同代的台湾人说,在“家就是工厂”的标语下,每天从学校回来就全家人围在一起做工。除了中国,60年代的学生动乱只是“发达国家”世界的体验。这也是此次在台湾开展帐篷戏剧的不可逃避的前提。
陈:六十年代的台湾,只有少数人通过美国留学的经验,特别受到68年美国左倾运动的影响。他们非常震惊,本来以为是土匪的国家,为什么外国人会开始重新评价毛泽东,胡志明,越南的革命。江青的样板戏,天安门,周总理等等,都在北美洲的电视上出现。所以给他们Shock很大。紧接着就是保钓运动。这是五十年代Red Patch以后,台湾的思潮第一次向左转。所以在北美洲有几个读书会,在美国的东亚研究所等地方,大家开始看中国革命的书,三十年代的书,思想上也起了很大的变化。所以我们从五十年代到六十年代,除了反共抗俄文学以外,就是Modernism的文学,所以当时受到Modernism影响的青年,到美国以后,受到68年的影响,就开始批判Modernism。1970年到1974年,台湾有一个现代诗批判运动,就是否定Modernism的诗歌。然后,在这个基础上,四十年代的左翼文学思想开始在七十年代乡土文学论战中登场。我个人的情况呢,就是因为偶然的机会,在旧书店里看到四十年代的书籍。当时我一个人跑到淡水那边,去听Transistor Radio。那时候,全中国一片红,叫嚣地非常厉害,毛主席党中央等等。还有“九评”,苏联共产党和中国共产党的论争。当时中国是把苏联的论文也广播,中国的回答也广播,一天广播两三次,我就躲在被窝里听。为什么到淡水呢,因为淡水离大陆比较近,听起来比较清楚。这是我个人比较特殊的体验。所以六十年代的风潮,文革起了作用。韩国在六十年代也有反对独裁的斗争,台湾也等于是间接受到文革的影响。
樱井:单只想象一下淡水河边,听收音机的陈映真先生的身影,好高大的感觉。(笑)
刚才提到启蒙的话题,在我开始帐篷戏剧时,已经没有启蒙的概念。当然传达的要素还是有,但至少根本感觉不到知识分子面向大众的感觉。不只如此,当时对知识分子性进行了激烈的否定,实际上也没有积累知识分子的训练。当然包括新左翼在内的左翼性中,启蒙这种概念很重要。但我们没有。
陈:具体来说,作为给劳动者看的演剧形式的帐篷剧,到底有多大的可能性?实际上,您觉得传达的怎么样?
樱井:我觉得传达到了。我们从77年左右至90年代,在东京的山谷、横滨寿町大阪的釜崎—劳动者聚居的街区,进行了活动。就是领日工资的劳动者的街区。演的不好,会有人乱扔东西,女演员一出场,观众就很兴奋,恨不得要抱住女演员。我们是一边护着女演员,一边让她们说台词。那真是很真实的身体感觉,哪有时间烦恼知识分子和大众之间的问题。那正是与劳动者在争夺“戏剧”,正是传达的场。我们这一侧誓死力争,那不顾一切要传达的一点点就很纯地显现出来。当时我们的演员很多就是领日工资的劳动者,或者过着相近的生活。我自己到四十岁为止就是领日工资的体力劳动者。在劳动现场工作的话,帐篷也越搭越顺手。并且,慢慢地,那些领日工资的劳动者的伙伴,开始给我们帮忙,领日工资劳动者的文化渐渐衍生出来。所以,如果说启蒙,在七十年代初期,是作为媒体的方法论出现的。媒体报道和商业主义很巧妙地剥夺了60年代的一切。所以,我们不做“启蒙”,并且为了时刻戒备着不被“启蒙”,只有自然地投向帐篷戏剧。
陈:这也是很深刻的地方。我看到大造先生这篇关于公共性的文章。没有疑问的是,资本主义越发展,市场化越厉害,公共性就越受到既有的制度化、平均化的影响,有这样一种危机。大造先生这篇文章就是在这种危机中,讨论如何还公共性一个清白。个人在公共性里面的主体性。我觉得这篇文章很有意思。“痒”和“痛”的辩证法的关系。还有一个就是,公共性中,主体性和全体性的辩证法的关系。可是像这样的一种思考,无论如何是知识分子的想法,这对大众来说,还是很难的吧。这很重要,怎么样把这样的一种思考,透过审美的方法,让民众能够理解。我所说的启蒙,也并不是高高在上的启蒙。像布莱希特所说的那样,艺术、文学、包括戏剧,从大众平常的生活来,表现的时候又高于生活。它不是从生活来,就那么原封不动地再表现出去。它来自生活,又高于生活。因为它凝练了生活,让群众知道生活中所隐藏的矛盾。然后现代公共性,在高度消费主义、市场主义里,每个人都觉得他们是市民、公民,其实他是被玩弄的。怎么样唤醒这一点?这是我读了大造先生的文章所感受到的有意思的地方。可这决不是很容易理解的东西。可是如何把这样好的想法,通过审美的方式还给群众,然后再从群众那里得到回馈。我的问题是在这里。绝对不是说,我赞成一个高高在上的精英阶层。
樱井:首先,也许我那篇《关于公共性的“痒”》的文章,对于普通人来说有些费解。可能因为我不高明,只能写硬硬的文章。所以说,普通人读了也难于理解。这没什么,有关诉诸笔端的东西。但,至于说演剧,我自信贯彻可以传达的表演。说到演剧,我在写剧本的时候,也经常与住在那片土地(搭帐篷的土地)上的老婆婆们碰面,脑子里一直浮现着她们的脸孔,一边在写。就是说,我坚信过着稍显艰难的生活的人们一定能看懂我的戏。当然是用了很难的语言。前面可能是说了比较费解的话,但后面一定会紧跟着有噱头。通过这种连环套式的结构,就能使前面难懂的语言清晰地呈现出来。我就是采用这样的方法。这和读书不同。也就是说,戏剧的语言是被翻了个个,而那些老婆婆们正是在这戏剧语言的“翻身”中,看着前面那些难懂的话。所以,重要的不在于语言本身,而在于在戏剧语言“翻身”的过程中,可以在一瞬间捕捉到相关的构图。从这个意义上说,应该是可以看明白。
陈:不过这个问题,我当然戏剧是不太懂。我想说,在文学里也有同样的问题。你有一个理念,但你不能赤裸裸地把它表现。你要想办法,想各种各样的办法。比如我写《山路》和《铃铛花》时,那时还是戒严时代,更不能赤裸裸地,我必须想一个故事,设定各种各样的情境,把我心里要讲的话讲出来。那这里就要自觉地提高审美要求,其实是一样的。我所要说的是,欧巴桑们所熟悉的艺术形式,所习惯的民间戏曲的形式,都是比较传统的。有开头,有中间,有结束,有人物的关系。这是民众艺术里,很平常的。然后我们用这种方法来让她知道(内容)。当然大造先生肯定也有他的道理。像布莱希特也不是完全用传统的方式,也是用断裂、跳跃,甚至于打破戏剧的幻觉,直接对观众讲话的方式。我的意思不是说,一定要用什么方法,我在问的是它的效果。布莱希特的方法,就是告诉你,我不是在演戏,是要告诉你一个道理。别人演戏的时候,希望你入戏,希望你哭一鼻子,然后受我的感动。可是布莱希特是故意破坏这个舞台的幻想,你必须起来,你必须觉醒,我们生活里存在什么样的矛盾。这当然是可以的。所以,我现在就是想说,大造先生“公共性”这三个字,在台湾的知识分子里面,能够理解的人也不是太多。那这个东西,拿到戏剧对白的里面,当然会有各种不同的理解。可是跟大造先生这篇文章里面所讲的相比,就显得不那么深刻。
樱井:我感觉布莱希特所说的演剧的“异化效果”是作为一种方法论被被纳粹所利用。布莱希特所挑战的可能是使大众觉醒,但那很快就原封不动地淹没在大众的狂热中。纳粹三十年代的十万人左右的即兴演剧集会,正是利用了布莱希特的理论。如果要追求“效果”,恐怕就会出现这样的问题。所以,我并不向戏剧谋求一种“效果”。当然是做排练和舞台的准备,但在那当中要发生什么,完全无法预想。我们更重视,那个场开始捉到那无法预想的视线。所以,离所谓的作品性较远。
陈:大造先生讲的很对。虽然我是抱着这样的疑问。可是我那天亲自去看,三个钟头没有冷场,这本身就说明什么。因为现在的观众不时那么容易讨好,他看不懂,就会很没有礼貌地走掉。所以那天,我自己当然看法是不一样,我每一个字都在认真听。虽然第二天排的不是很熟练,但那样的剧场能够维持三个小时,笑得那么开心,这本身就说明问题。大造先生虽然用的是比较实验性的手法,可是就像您刚刚所说的,不见得这样的手法,观众就完全不能进入那个世界。每一个人也许进入的方法不太一样,可是三个小时维持下来,是很不容易的事情。我另一个发现就是,大造先生是一个艺术家,是一个文学家。我后来读剧本的时候,有好几个段落,都是很有诗意的叙事,非常的优美。比如说,妈妈要被叫出去时,希望有更多的时间喂孩子。看到那里,眼眶都红了。还有好几个,我都有记下来。所以我都怀疑大造先生是写诗的。但我不知道您是否每次创作都像这次这样匆忙,还是因为来台湾的原因。如果能有更好的彩排,每个人都知道他在做什么,那样,那个传达就会更好。
樱井:您太过奖了。从陈先生观看的第二天的戏开始,到昨天是第五天,已经很进入状态。
关于排练不足,确实如此,这也正是业余演剧的宿命。特别是,此次创作集体的集中方式比较特别。我邀请的人只有钟乔和王墨林。这两个人基本上没有表演经验。整体来说,大家就是靠缘分很自然地走到一起。十七个演员有表演经验的只有一半左右。生下来第一次演戏的人占一半。一个戏里面,用十七个角色性格来排列组合,非常困难。而且都是主角,但并不是不可能。只要有强韧的要传达那些演员的意志,总可以尽力到一定程度。所以,与演剧的资质等无关,那个人为什么要站在戏剧的场上,在何种身体上有变化的可能性,这些才是重要的。我只是把无法变作那个人语言的意志翻译,并想办法在那个场使之升华。当然可能大部分是误读·误解,只要我有翻译的欲求,那误读就在排练场生出下一个美丽的误读。如果说我的剧有富有诗意的地方,那是在写那个人的时候,误读·误解中的痛苦开融时,语言就一下脱颖而出。并不是在我自身中单独产生诗意。
陈:我还有一点感觉就是,像“Faust”这个题目,戏剧上我不太清楚,在文学上都被不断地再生产。想要有无限的知识,用他的生命和灵魂去交换。出卖他的灵魂,来换取财富、美女。
可是,在大造先生的作品里面,他完全打破了这种因循的做法。原来的主题变得并不重要。虽然也出现了“Faust”、“Mefist”和那个少女,但已经完全不是那么一回事。我刚才也讲过,如果演员再有一点时间的话,会传达的更好。
樱井:我在台湾搞帐篷剧是第一次,当然非常希望多排练,但几乎没有留给排练的时间。我自己一直要挖洞,做舞台几乎没有吃饭的时间。因为大家没有经验,不知道怎么做。就是进行说明,也还是不能完全理解,出了问题的话,是非常危险的。我就不得不自己做。当然,我已经和台湾的人们打了五年的交道。在这五年中,台湾的人们有很大变化。最开始在台湾搭帐篷时,我自己在现场挖地,媒体来采访,问“导演是谁”,我就回答“是我”,结果遭到一脸不屑的表情。与其说这是台湾模式,更重要的是,这样的事(导演自己挖地)做不得的意识观念,在台湾人的身体里有深深的烙印。大家都还不能从这种束缚中解脱出来。像搬运东西等等,稍微脏一点的活,是绝对不做的,那些搞戏剧的高级人才们。曾经有过很哭笑不得的经历。开始搭帐篷的时候,堆了一堆沙子,需要把这堆沙子移动一米左右的距离。我就问当时在场的人帮忙,不料,大家拿出手机,叫搬运公司的人来做。只是一米的距离呀,好像台湾这一百年的历史都在里面。
陈:我在这里再讲一点,就是关于六张犁公墓的事情。六张犁公墓最开始发现的几个人当中,就有我。我们和那些老政治犯一起去那个公墓,拔草。后来就一个一个发现那些墓碑,三个区,一共两百多个。所以,大造先生的戏一开始就是墓地的场景,对我的Impact非常大。还有一点就是,大造先生的戏当中,经常出现的监狱、墙壁、没有门(No Exit),这种感受对我来说,特别强。因为也许牢房里有一个门,可是门对你没有意义。狱卒在外面开的时候,那个门才是开的。还有就是那个妈妈奶孩子,人都要枪毙了,就希望多奶一下孩子。像这样的东西,对我这个曾经在牢里生活过,听了很多故事的人来说,感觉非常强。所以,结束的时候,我为什么要站起来鼓掌。对我来说,这是非常非常激动的。
樱井:当然这些情节正是从陈映真先生的作品《赵南栋》中得到的启发。
陈:还有一个是,死刑犯快要被枪决。叫她蒙眼睛,她不蒙,叫她去手铐,她不去。还有看那个河流,这个对我来说,太熟悉了,我自己也写过。
樱井:是这样。我有一次去马场町的时候,就那么静静地望了一阵子眼前的河流,我后来写进剧本的风景,就浮现在眼前,河中的小船等等。当然这对我来说很重要,但如果直接描写的话,会有强加于人的感觉。比如,即使直接向观众说,“那真是不堪回首”,恐怕也很难有共鸣。所以先铺陈上其他的东西,然后在出其不意的地方稍作点染,就会很熨烫地进人的心田,可以有共鸣。对我来说是这样,应该对观众来说也是一样吧。像监狱的场景,看起来有点梦幻的感觉,但其实,如果真的能让观众再能有更上一层楼的理解,对那个场,那就算小小的成功吧。最后的处刑的场景等,好多来帮忙的年轻人都禁不住掉泪,大家还是有感觉的。这不正很重要吗。还有作为一直以来,流传甚广的在监狱中目送死囚的场景。那是从蓝博洲先生的《幌马车之歌》中,“用《幌马车之歌》送我吧”的细节中得到的启发。在这次我的戏里,赴死刑的是女人们,我就发现了“眉飞色舞”这个话。像“白名单”那样的“没有名字的”人们,目送死者时,也用的是“眉飞色舞”这个话。
陈:可以想象,您自己一边创作,一边感动自己。
樱井:倒不是这种意思。不可思议的是,我自己把剧本写下来的瞬间,在把它传给胡小姐(剧本的翻译者)的同时,日文的剧本就消失了。作为剧本,已经变得没有社会性的意义。如果在日本,最起码到公演开始时,剧本还是需要的。可是在台湾,就很不可思议,日文的剧本在传给翻译者的瞬间,就已经不再被需要了,百无一用。也没有必要再留下来。剧本本身已经穿透演员的身体,也就是说,演员在活生生地吃掉剧本,肯定有什么东西会留下来,至少三十年忘不了。一瞬而已。现实当中,可能会发生更大的事情,但戏剧真是瞬间的胜负。这和读了文学作品,让人感动,难以忘怀,是一样的吧。就是一种体感。
陈:不过,戏剧和小说不太一样。小说可以用书的形式一直流传下来。戏剧呢,演过了,第二场、第三场,解释也不一样。所以,正因为演出的解释会不同,剧本还是很重要。
樱井:但我写的可能只算是混混文学,也不可能有第二次。至今为止,从来没有重新上演过。本身也绝对不可能。好像刚才说的,剧本是按演员量体裁衣的,并且是他(她)现在的体。即使是同一个人,过了一年,已经变成另外一个人了,以前的东西,不可能再合适。可能确实有些虚无,真是短期的剧本的创作,稍纵即逝。
休息后,对谈再次开始。
樱井:刚刚听说,陈映真先生六十年代曾经创办过《剧场》杂志。您当时是否被称为现代主义者。
陈:在六十年代的时候,在Red Patch和戒严令下,Modernism有两个功能。一个是,Modernism不会触及现实。它不谈社会,不谈人,不谈问题。“反共抗俄”文学又是种指令性的枯燥的东西。这是第一个原因。第二个原因是受美国影响。美国新闻处(USIS),所有的冷战文化以美国为中心,透过各地的USIS,来输出美国式的Modernism。所以当初的年轻人,都受到那个影响。剧场也是那样。剧场里面就有分裂。因为我跟一个叫刘大任的,思想上不太一样。我们是搞现实主义的,所以,杂志就分裂了。
今天从大造先生那里讨教了不少。我感觉到了剧场的魅力。我就是对很简单的东西,也很容易感动。我去看游园会,小孩子演狼外婆的故事,这故事我们熟的不得了。小红帽见到这个危险,就叫妈妈,我的眼泪都要掉了。我就觉得很奇怪,怎么会这样。还是剧场有它不可思议的魅力。
樱井:日本的反体制戏剧(Under Ground Play)在六十年代时,都遭到资本的收买。全被改造成可以被商业主义所利用。所以,我们所作的,不如说,更接近于三十年代的东西。既然处在一种被剥夺的位置,那么除了竭尽全力不被资本所收买之外,别无选择。在商业主义的气氛中,没有人会演在墓地挖坑的戏。所以,这样的领域就幸存下来。日本的西武资本在六十年代就一眼盯上了剧场。在六十年代后半期,简直就是要把帐篷戏剧买断。就是收买,让剧团在西武自己的空地上演。然后,给钱,帐篷上就印着西武的标志。
陈:那个时期,台湾也有类似的情况。
樱井:所以,那正是我们斗争的出发点。那时,西武也曾来我这里几番游说。要说,我们能从西武的诱劝中脱身,还多亏了有天皇在。因为我们的戏里,一定有割天皇首级的场面,所以,才得以从资本的诱惑中脱身。如果没有天皇在,也说不定我们也会滑向那一方。真要感谢天皇相助,感谢裕仁天皇。
陈:因为天皇,戏剧得以幸存下来。
樱井:在当时七十年代、八十年代,真的是绝对的禁忌,现在也没什么人做。西武是与天皇一族保有关系来壮大资本的。有意思的是,当时从西德有人来邀请我参加戏剧节,我本身是反对戏剧节的形式,不打算去。但稍后,对方突然停止了邀请。原来因为出资的是西武。西武那边放出话来,绝对不能让那个割天皇首级的樱井去!
陈:台湾也是,在戒严时期,没有戏剧。戒严令解除以后,非常多的小剧场出现,那马上就被收买。跟日本那么长时间的斗争不一样。没有日本那种自我斗争的经验。
樱井:当时的右翼团体,其实并不把我们放在眼里。但公演之前还是会打电话来。“据说你们在戏中对天皇陛下有不敬!”。我们就回答“是这样”。然后对方会说“我们会过去!”,我们就回答“恭候光临”。
陈:日本的战后和台湾的战后情形完全不同。
樱井:还是我们的帐篷戏剧带出了亚洲的感觉。具体在我个人的层次上说,还是通过天皇,从而不得不意识到东亚的历史、日本与殖民地之间的关系。所以,从这个地方,开始自我批判。这在当时对日本的左翼来说,也是不能碰的东西。因为一说到天皇,左派的理论几乎无法成立。左派也不想碰天皇。反正觉得天皇会自生自灭,不用管他。当时有一个人企图爆炸天皇所乘列车(抗日武装战线),我们也在戏里有所反映。后来,左翼也对我们的做法面露难色。所以,我们当时乐得连左翼也忽视我们。共产党就不用说,连新左翼也排斥我们。
陈:我们台湾就不太理解,为什么日本的共产党和社会党终于都垮掉了。而且受到革新势力的排斥。影响很大。是因为教条主义的关系吗?
樱井:也有,还有就是,日本左翼里面的思想内容与亚洲的关系如何。它的现代主义,还有从西方输入的一些思想,比较难解释。我们是在比左翼还低的地方。所以尽管我被称作是日本人,但很难代表吧。在左翼之下,也就是在人之下。当然还是有伦理观的问题。年轻的世代对自己能上大学的事实,感到非常羞耻,那种与大众的反差。自己通过竞争,追求好日子。但这问题去仅仅停留在伦理观的层次上。问题是,日本的左翼没有能创造出超越伦理的思想。所以说,就看左翼之下的人是否能做。
最后还想说的是,经丸川先生介绍的陈映真先生的作品《忠孝公园》,我们去年让参加“台湾浮士德”计划的全体人员都读了这部作品。在这之前,台湾的朋友们都没读过。最后还是通过日本人,才读了。真是逆向输入。我们大概一个月一次,进行看似与戏剧无关的讨论。讨论的成果,最后还是表现在戏里面。所以说,实际上陈映真先生的小说,是我们此次演剧的坚实的基础,好像深埋在地下,我们在现场进行各种作业时,仿佛能看见陈映真先生的脸庞。
陈:不敢当,那我深感荣幸。今天从樱井大造先生这里受益匪浅,非常感谢。
樱井:谢谢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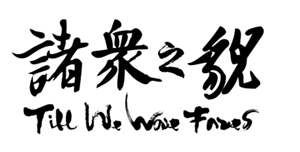

 微信扫一扫,打赏作者吧~
微信扫一扫,打赏作者吧~




發表迴響